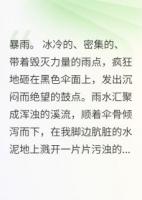《骨灰成妆:我为白月光捧骨灰盒》 精选章节 在线阅读
暴雨。冰冷的、密集的、带着毁灭力量的雨点,疯狂地砸在黑色伞面上,
发出沉闷而绝望的鼓点。雨水汇聚成浑浊的溪流,顺着伞骨倾泻而下,
在我脚边肮脏的水泥地上溅开一片片污浊的水花。
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土腥味、劣质香烛燃烧的呛人烟气,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被雨水冲淡却依旧顽固的…焦糊味。我站在送葬队伍的最边缘,
像一块被遗忘的、湿透的抹布。身上是临时借来的、不合身的黑色连衣裙,
粗糙的布料摩擦着我冰冷的皮肤。雨水打湿了额前的碎发,黏在脸上,冰凉刺骨。
没有人看我,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前方那个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黑色棺椁上,
聚焦在棺椁旁那个一身肃杀黑衣、如同地狱修罗般的男人身上。顾沉舟。
他撑着一把巨大的黑伞,伞沿压得很低,遮住了他大半张脸,
只露出一个线条紧绷、毫无血色的下颌。雨水顺着他挺直的鼻梁滑落,
滴在他剪裁完美的黑色西装肩头,晕开深色的印记。他站得笔直,
像一柄插在泥泞里的、淬了寒冰的剑。那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生人勿近的阴鸷和毁灭气息,
让周围所有试图靠近安慰的人,都噤若寒蝉,自动退开一个真空地带。棺椁里躺着的,
是沈清漪。顾沉舟心尖上的白月光,顾家默认的未来主母,也是…三天前,
死在我家那场冲天大火里的女人。三天前的深夜,那场毫无征兆、吞噬一切的烈火,
烧红了半个贫民窟的天空。木质结构的破败老屋,在汽油的助燃下,顷刻间化为炼狱。
尖叫声,哭喊声,木材爆裂的噼啪声…混乱中,我只记得一双冰冷如铁钳般的手,
死死地扼住我的喉咙,将我像破麻袋一样拖出火海,狠狠掼在冰冷的泥水里。然后,
就是顾沉舟那张在火光映照下、扭曲如恶鬼的脸。他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里面翻滚着足以焚毁一切的暴怒和…一种令人骨髓冻结的、失去挚爱的疯狂痛楚。“苏晚!
”他的声音嘶哑破碎,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每一个字都淬着剧毒的冰碴,“清漪在哪?
!她要是少了一根头发…”他猛地俯身,带着浓重血腥味和烟熏火燎气息的手,
如同鹰爪般狠狠攫住我的下巴,力道之大,几乎要捏碎我的颌骨!冰冷的剧痛传来,
混杂着窒息感,让我眼前阵阵发黑。我被迫仰起头,
对上他那双被怒火和绝望烧得通红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一丝人类的温度,只有毁灭的深渊。
“她一根头发,”他凑近,滚烫的、带着血腥味的呼吸喷在我脸上,
声音低沉如恶魔的低语,清晰地穿透火场的喧嚣和暴雨的嘈杂,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铁钉,
狠狠凿进我的耳膜,“比你全家…不,比你们整个贫民窟**胚子的命…都金贵!
”“轰隆——!”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铅灰色的天幕,
紧随其后的炸雷仿佛就在头顶炸开,震得脚下的大地都在颤抖。
惨白的光瞬间照亮了顾沉舟那张英俊却因极致的恨意而扭曲的脸,
也照亮了他眼中我那张苍白、狼狈、布满烟灰和泥泞、如同蝼蚁般渺小的倒影。闪电过后,
是更深的黑暗和更狂暴的雨。顾沉舟猛地甩开手,我像一滩烂泥般重新摔回冰冷的泥水里,
呛咳着,下巴和喉咙**辣地疼。他不再看我一眼,像一头彻底失去理智的困兽,
对着身后黑压压的保镖发出野兽般的咆哮:“找!给我掘地三尺!把清漪找出来!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保镖们如同黑色的潮水,顶着瓢泼大雨,
再次冲向那片依旧冒着滚滚黑烟、散发着皮肉焦糊味的废墟。三天。整整三天。
顾沉舟像疯了一样,调动了顾家所有能动用的力量,封锁了整片区域,
几乎将废墟的每一寸焦土都翻了过来。最终,只在主卧位置的残骸深处,
挖出了一个被高温熔得变形、勉强能辨认出形状的…金属保险箱。里面,
是一捧混合着建筑粉尘、辨不出原貌的灰白色粉末。那就是沈清漪。
顾家高高在上、圣洁无暇的白月光,最终化成了眼前这个小小的、冰冷的檀木骨灰盒里,
一抔肮脏的灰烬。“起灵——!”司仪带着哭腔的嘶哑喊声,穿透了密集的雨幕。
沉重的棺椁被八个壮汉抬起。哀乐呜咽着响起,夹杂在暴雨的轰鸣里,显得格外凄厉悲凉。
送葬的人群开始蠕动,像一条黑色的、沉默的蠕虫,缓慢地挪向墓园深处。我依旧站在原地,
冰冷的雨水顺着发梢、脸颊、脖颈,不断流下,浸透了单薄的衣衫,冷意刺骨。
目光却不受控制地黏在那个被顾沉舟亲手捧在胸前的、小小的黑色檀木盒子上。
那个盒子…那么小,那么轻。里面装着顾沉舟的命,装着我的…催命符。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刺骨、带着实质般杀意的目光,如同淬毒的利箭,穿透雨幕,狠狠钉在我身上!
是顾沉舟。他不知何时停下了脚步,站在送葬队伍的前方,隔着重重雨帘和攒动的人头,
转过身,那双深不见底、如同万年寒潭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
雨水顺着他冷硬的侧脸线条滑落,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片死寂的冰冷,
和眼底翻涌的、毫不掩饰的、刻骨的憎恨。他微微抬了抬下巴,动作极其轻微,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站在他身侧、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白手套、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立刻会意。
他面无表情地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厌恶,
仿佛看着什么肮脏的秽物。他没有说话,
一直捧着的另一个黑色檀木盒子——那个装着沈清漪骨灰的盒子——以一种近乎施舍的姿态,
递到了我面前。冰冷的檀木触感透过手套传来。我僵在原地,血液似乎瞬间冻结。
周围的目光,或同情,或好奇,或幸灾乐祸,像无数根细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身上。
管家见我不动,眉头不耐地皱起,声音冰冷平板,如同机器:“苏**,请。
”那声音不高,却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我的脸上。所有的尊严,所有的羞耻,在这一刻,
被碾得粉碎。我颤抖着,伸出同样冰冷僵硬的手。指尖触碰到那光滑冰冷的檀木盒面,
一股难以言喻的恶心感瞬间涌上喉头。我死死咬住下唇,用尽全身力气,
才没有当场呕吐出来。双手,如同捧着千斤巨石,又如同捧着烧红的烙铁,
极其缓慢地、极其沉重地,接过了那个小小的、却承载着滔天罪孽和无穷恨意的盒子。冰冷,
沉重。那里面,是顾沉舟的心头血,也是悬在我头顶的、随时会落下的断头铡。
管家面无表情地退开。顾沉舟远远地看着,
看着我卑微地、如同捧着圣物般接过那个骨灰盒。他那双深潭般的眼眸里,憎恨之外,
终于掠过一丝极其隐晦的、扭曲的快意和…掌控。他转过身,不再看我,重新迈步,
走向墓园深处。黑色的背影在暴雨中,如同移动的墓碑。我捧着那冰冷的盒子,
如同捧着自己的灵位,一步步,踏着泥泞,跟在送葬队伍最后面。每一步,
都像踩在烧红的炭火上。雨水混合着屈辱的泪水,无声地滑落。沈清漪的名字,
顾沉舟那句“一根头发比你全家命都金贵”的诅咒,如同跗骨之蛆,反复啃噬着我的神经。
从那天起,苏晚死了。活下来的,
是顾沉舟脚边一条没有名字、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狗。顾家祖宅,“归尘苑”,
成了我华丽的金丝笼,也是冰冷的刑场。我住进了最偏僻角落的佣人房。房间干净整洁,
甚至称得上雅致,有独立的卫浴,比贫民窟的破屋好了千百倍。但这里的空气,
每一寸都弥漫着无声的压迫和监视。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沉默如影的保镖,
佣人们表面恭敬实则鄙夷疏离的眼神…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我死死困住。
我的“工作”只有一个:照看沈清漪的灵堂。那是“归尘苑”西翼尽头,
一个常年点着长明灯、供奉着新鲜百合的静谧房间。房间中央,黑色大理石基座上,
摆放着那个小小的、我亲手捧回来的檀木骨灰盒。盒子上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
画中的沈清漪,穿着洁白的纱裙,站在一片盛放的百合花丛中,回眸浅笑。
阳光勾勒着她精致的侧脸,眼神清澈纯真,如同不谙世事的天使。她的美,
是那种毫无攻击性、让人心生怜惜的圣洁。尤其是那双眼睛,如同浸在水中的琉璃,
纯净得不染一丝尘埃。每天清晨,我需要用特制的软毛刷,
极其小心地拂去骨灰盒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更换长明灯的灯油,
确保那豆大的火苗永不熄灭。花瓶里的百合,必须是最新鲜、花瓣上没有一丝瑕疵的极品,
每日一换。房间里的熏香,是沈清漪生前最爱的“空谷幽兰”,味道清冷孤绝。
每一次踏入这个房间,每一次触碰到那个冰冷的骨灰盒,
每一次抬头看到画中人那纯净无垢的微笑,
顾沉舟那句恶毒的诅咒就会在耳边尖锐地回响:“她一根头发,比你全家的命都金贵!
”每一次,都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我早已麻木的心脏。顾沉舟很少出现在灵堂。
但每次他来,都像一场无声的审判。他会长时间地站在那幅油画前,背影沉默而孤寂,
周身散发着浓得化不开的哀伤和戾气。有时,他会伸出手,指尖极其轻柔地拂过画框边缘,
仿佛在触碰情人温热的肌肤。那动作里的珍视和温柔,与他看向我时那如同看垃圾般的眼神,
形成地狱与天堂的对比。而我,只能垂着头,屏住呼吸,如同最卑微的尘埃,
缩在房间的角落里,等待他离开的命令,或者…一时兴起的“惩罚”。“苏晚。
”他的声音总是毫无预兆地响起,冰冷,没有起伏,却能瞬间冻结我的血液。
我立刻像被鞭子抽到一样,僵硬地站直,垂着眼,不敢看他。“清漪不喜欢灰尘。
”他可能只是陈述。我立刻跪下,用雪白的丝帕,
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直到膝盖麻木。“这百合,香气太浊。
”他或许只是皱眉。我会在寒冬深夜,被勒令立刻去暖房,
找出最新鲜、香气最纯净的那一支,哪怕双手冻得通红发僵。最“温和”的惩罚,
是他什么也不说,只是用那双深不见底、毫无温度的眼睛,长久地、沉默地注视着我。
那目光像无形的冰锥,刺穿我的皮肉,直抵灵魂深处,拷问着根本不存在的“罪行”。
在那样的注视下,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难熬。我变得异常沉默。
像一尊会呼吸的、没有灵魂的雕像。除了必要的应答,几乎不再开口说话。眼神空洞,
表情麻木,对所有指令都温顺地服从。顾沉舟让我往东,我绝不会往西。他让我跪下,
我绝不会站着。顾家的佣人们私下议论。“看,那就是害死沈**的罪人…”“活该!
顾先生留她一命,已经是天大的仁慈!”“跟个行尸走肉似的…晦气!”我充耳不闻。
所有的感官,所有的情绪,似乎都被抽离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躯壳,
日复一日地擦拭着那个冰冷的骨灰盒,供奉着那个画中的“天使”。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每一个死寂的深夜,当“归尘苑”陷入沉睡,只有灵堂那盏长明灯幽幽燃烧时,
我蜷缩在冰冷坚硬的佣人床上,睁大眼睛望着无边的黑暗。指甲会深深掐进掌心,
直到渗出血珠,带来一丝微弱的、证明自己还活着的痛感。那场大火前的记忆碎片,
会在黑暗中不受控制地翻涌上来——母亲枯瘦的手死死抓着我的手,
浑浊的眼睛里是深不见底的恐惧和绝望。
“晚晚…跑…快跑…别管我…他们…他们不是人…”“轰隆——!”巨大的爆炸声浪。
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浓烟呛得人无法呼吸。
一双冰冷如铁钳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还有…火光映照下,
一张模糊却充满恶意的脸…这些碎片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灵魂都在抽搐。
仇恨如同剧毒的藤蔓,在麻木的躯壳深处,在每一次对骨灰盒的擦拭中,
在每一次承受顾沉舟冰冷目光的屈辱里,无声地、疯狂地滋长着。
它汲取着我每一滴屈辱的泪水,每一丝麻木的痛楚,缠绕着我的心脏,勒紧我的骨骼,
在死寂的温顺外表下,酝酿着一场足以焚毁一切的黑色风暴。
沈清漪…顾沉舟…我空洞的目光,落在灵台上那幅纯净美好的画像上,
落在那个冰冷的檀木盒子上。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时间在“归尘苑”死水般的沉寂中,
流淌得格外缓慢。日历一页页翻过,季节无声更迭。庭院里的银杏叶黄了又落,
落了又生新芽。唯有西翼灵堂里的长明灯,日复一日,幽冷地燃烧着,
映照着那幅永不褪色的圣洁画像,和画像下那个沉默冰冷的檀木盒子。我的存在,
像空气里的一粒尘埃,被所有人习惯性地忽略。
顾沉舟似乎也渐渐“习惯”了我的温顺和沉默。他来灵堂的次数少了,即使来,
也多半是沉默地站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很少再对我发出指令。
那种令人窒息的、带着审视和惩罚意味的注视,似乎也淡了。佣人们偶尔的议论,
也从最初的鄙夷和唾弃,变成了麻木的习以为常。“那个罪人”成了我在顾家的代名词,
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活体摆设。直到那个深秋的下午。空气里弥漫着清冷的菊香。
我像往常一样,跪在灵堂光洁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用雪白的绒布,
极其轻柔地擦拭着那个承载着沈清漪骨灰的檀木盒子。动作一丝不苟,
虔诚得如同在擦拭世间最珍贵的圣物。阳光透过高窗,斜斜地照射进来,
在盒面上投下一道温暖的光斑。沉稳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走廊外响起,由远及近。我的心跳,
毫无征兆地漏跳了一拍。是顾沉舟。这个时间,他很少过来。脚步声停在门口。我没有抬头,
依旧专注地擦拭着,只是脊背下意识地绷紧了些。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走向那幅油画。
脚步声停在了我的身侧。一股熟悉的、带着冷冽松柏和昂贵雪茄混合气息的压迫感,
无声地笼罩下来。我甚至能感觉到他落在我头顶的、那道深沉莫测的目光。
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秒。然后,一只骨节分明、异常干净的手,伸到了我的面前。
那只手,曾扼住我的喉咙,曾捏碎我的下巴,曾无数次对我下达冰冷的指令。此刻,
它却稳稳地平摊着,掌心朝上。在掌心中央,一枚戒指静静地躺在那里。
不是常见的璀璨钻石。那是一颗极其罕见的、深邃如海洋的蓝钻。鸽卵大小,
被完美地切割成水滴形,镶嵌在繁复而古老的铂金戒托上。幽蓝的光芒在斜射的阳光下流转,
深邃、神秘、冰冷,仿佛蕴藏着整片星空,又像是凝固的深海之泪。美得惊心动魄,
却也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非人间的寒意。我的呼吸瞬间停滞。大脑一片空白,
像被投入了绝对零度的冰海。血液似乎都停止了流动,
全身的感官只剩下那枚散发着幽蓝寒光的戒指,和头顶那道如同实质般的、审视的目光。
他要做什么?顾沉舟没有说话。他只是维持着那个摊开手掌的姿势,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如同两口幽深的寒潭,
清晰地映出我此刻僵硬的、毫无血色的脸和眼中无法掩饰的惊骇。沉默,如同沉重的铅块,
压得人喘不过气。几秒钟后,他动了。那只拿着戒指的手,缓缓地、不容抗拒地,
伸向了我的左手。冰冷的金属触感,带着他指尖微凉的温度,落在了我的无名指指根。
我的身体猛地一颤,像被毒蛇咬了一口,本能地想要缩回手!“别动。”低沉平缓,
却带着绝对命令意味的两个字,如同冰锥,瞬间冻结了我所有的反抗。
他的手指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稳稳地捏住了我的指尖。动作谈不上温柔,
甚至带着一种惯有的、掌控一切的强势。那枚冰冷的、幽蓝的戒指,
被他缓慢地、却无比坚定地,推过我的指节,最终,牢牢地套在了我的无名指根部。
尺寸…竟然分毫不差。幽蓝的宝石紧贴着我的皮肤,传来一种奇异的、冰冷的灼烧感。
那深邃的光芒,映着我苍白的手指,形成一种极其诡异又刺眼的对比。我僵硬地抬起手,
目光呆滞地看着无名指上那枚突然出现的、象征着某种可怕契约的冰冷信物。
巨大的荒谬感和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如同冰冷的藤蔓,瞬间缠绕住我的心脏,
勒得我无法呼吸。顾沉舟终于收回了手。他依旧站在我身侧,
目光从我戴着戒指的手上移开,重新投向灵台上那幅圣洁的画像。
他的侧脸线条在光线下显得冷硬而深刻,薄唇紧抿,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情绪,
仿佛刚才只是完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下月初八,”他终于开口,
声音依旧毫无波澜,像在宣布一个与己无关的决定,“订婚宴。”说完,
他没有再看我一眼,也没有再看那骨灰盒一眼,转身,迈着沉稳的步伐,离开了灵堂。
沉重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尽头。死寂重新笼罩了灵堂。只剩下我,
依旧僵硬地跪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左手无名指上,那枚幽蓝的“深海之泪”戒指,
散发着冰冷而妖异的光芒,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又像一个来自深渊的诅咒。阳光透过高窗,
将我和那个冰冷的骨灰盒,还有画中微笑的沈清漪,一起笼罩在温暖的光晕里。
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只有刺骨的冰寒,从指尖那枚冰冷的戒指,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
订婚…宴?和谁?和我?这个害死他心尖白月光的“罪人”?荒谬!疯狂!
巨大的恐惧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被更深阴谋笼罩的寒意,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吞没。
我看着那枚戒指,看着画中沈清漪纯净无垢的笑容,
再低头看看那个冰冷的骨灰盒…顾沉舟…你到底想做什么?
“深海之泪”冰冷的触感如同跗骨之蛆,时刻提醒着我那场荒谬的“订婚”预告。
顾沉舟丢下那枚戒指和那句命令后,便如同人间蒸发,再未踏足灵堂一步。
但整个“归尘苑”的气氛,却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死水,表面依旧沉寂,底下却暗流汹涌。
佣人们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不再是单纯的鄙夷和疏离,
是混杂着极度的震惊、难以置信、以及一种深重的、仿佛看到秽物玷污圣殿般的恐惧和厌恶。
他们远远地避开我,像避开瘟疫的源头。偶尔的窃窃私语,也如同毒蛇的嘶鸣,
钻进我的耳朵。“她?顾先生的未婚妻?疯了吧?”“沈**尸骨未寒啊!
顾先生怎么能…”“肯定是这个**用了什么下作手段!迷惑了顾先生!”“天理难容!
沈**在天之灵不会安息的!”这些声音,如同淬毒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心上。
但我依旧沉默,依旧麻木。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木偶,
每日重复着擦拭骨灰盒、更换百合、添灯油的机械动作。只是每一次低头,
看到无名指上那抹幽冷的蓝光,心脏都会不受控制地剧烈抽搐一下。那枚戒指,
像一个冰冷的嘲讽,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顾沉舟的姐姐,顾沉薇,
是在一个阴沉的午后,带着一身凛冽的寒气踏入灵堂的。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
清脆、急促、带着毫不掩饰的愤怒。她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深灰色套装,
妆容精致却掩盖不住眼底的阴鸷和怒火。保养得宜的脸上,此刻因愤怒而微微扭曲,
那双和顾沉舟有几分相似的狭长眼眸里,燃烧着熊熊的恨意,像两簇淬了毒的火焰,
直直射向我。她甚至没有看一眼沈清漪的画像和骨灰盒,目标明确地冲到我面前。
“啪——!”一声极其清脆响亮的耳光,狠狠掴在我的脸上!力道之大,
打得我整个人猛地一个趔趄,脸颊瞬间**辣地肿起,嘴里泛起浓重的血腥味。
耳朵嗡嗡作响,眼前金星乱冒。“**!”顾沉薇的声音尖锐刻薄,带着浓重的恨意,
像淬了毒的冰锥,“你用了什么妖术?!给我弟弟灌了什么迷魂汤?!清漪才走了多久?!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戴上顾家的戒指?!也配做沉舟的未婚妻?!
”她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狠狠戳向我戴着戒指的手,指甲几乎要划破我的皮肤。
我踉跄着站稳,垂着头,脸颊肿痛,嘴里满是铁锈味。没有辩解,没有反抗,
甚至连捂脸的动作都没有。只是沉默地承受着。如同过去无数个日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