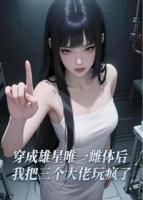夜色,浓得化不开。王风推开那扇厚重的、雕着繁复花纹的卧房门时,
身上还带着从外面裹挟进来的、初秋夜晚的凉意,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酒气。不是应酬,
是他独自在书房喝的,为了压下心头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房间里,灯火通明,
过于亮堂,刺得他微微眯了下眼。大红的床品,鸳鸯戏水的苏绣被面,
桌上摆着成双的龙凤喜烛——尽管那蜡烛只是装饰,并未点燃。
一切都在刻意营造着“洞房花烛”的氛围,俗气,又带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强制意味。空气里,
弥漫着新家具的皮质味道,还有一种极淡的、陌生的花香调香水气息。他的新娘,白凤,
就坐在那张过分宽大、铺陈着浓烈红色的床沿。她穿着一身质地精良的红色旗袍式礼服,
勾勒出纤细的腰身,头发规规矩矩地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段白皙脆弱的脖颈。
她低着头,双手安静地交叠放在膝上,像个等待命运宣判的、精致却无生气的瓷娃娃。
王风的视线在她身上停留了不到两秒,便漠然地移开。
他扯了扯颈间那条束缚了他一整天的领带,动作带着不耐,径直走到她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
真皮沙发发出轻微的陷落声。他没有迂回,甚至没有一句客套的寒暄,
直接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份折叠整齐的文件,指尖一推,滑到两人之间的矮几上。
纸张与玻璃桌面碰撞,发出清晰的“啪”一声。“白**,”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
带着浸透夜色的凉,“这是协议。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白凤似乎被那声响惊了一下,
肩膀几不可察地微微一颤。她终于抬起头。灯光下,她的脸很小,皮肤很白,
是一种缺乏血色的、近乎透明的白。五官生得极好,是那种江南水乡般的清丽婉约,
尤其一双眼睛,大而黑,眼尾天然带着一点点下垂的弧度,看人时,
总像含着几分怯生生的、未经世事的茫然。此刻,这双眼睛里,除了茫然,
还有一丝努力压抑下去的什么情绪,太快,王风捕捉不到,也懒得去捕捉。
她的目光掠过桌上那份标题加粗的《婚后协议》,最后,落在王风没什么表情的脸上。
王风迎着她的视线,语气平稳,却字字如冰锥:“我们这场婚姻因何而来,你我心知肚明。
不过是两家利益结合的产物,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他顿了顿,
刻意忽略掉她骤然攥紧了旗袍下摆的手指,继续道,
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冷酷:“协议期限三年。三年之内,在人前,
你需要扮演好王太太的角色,维护两家颜面。私下里,我们互不干涉,保持距离。
”他的目光在她脸上逡巡一圈,像是在确认她是否听懂了这残酷的规则,然后,吐出最后,
也是他认为最核心的警告:“别对我,对这段关系,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
感情。”最后两个字,他咬得格外清晰,带着明确的切割意味。空气仿佛凝滞了。
只有窗外远处城市永不熄灭的霓虹灯光,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
在昂贵的地毯上投下一条变幻的、微弱的光带。白凤静静地听着,长长的睫毛垂下去,
在下眼睑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也没有被羞辱的愤怒,
只有一种近乎认命的平静。沉默在房间里蔓延,带着无形的压力。几秒后,她伸出手,
拿起了那份协议。她的手指纤细,指尖透着淡淡的粉,微微有些发抖。协议条款并不长,
但条条框框,界限分明。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财产独立,隐私互不侵犯,
以及最重要的——三年后,无条件离婚,
男方会给予女方一笔足够她后半生衣食无忧的补偿金。她看得很慢,一页,一页,
翻动纸张的声音,在过分安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王风靠在沙发背上,耐心地等着。
他看着她低垂的侧脸,看着她紧抿的、没什么血色的唇瓣,心里莫名地升起一丝烦躁。
他讨厌这种被安排的感觉,讨厌这个被硬塞进他生命里的、来自所谓“贫民窟”的女人。
尽管调查资料显示她背景简单,性子怯懦,最好拿捏,但他依然觉得碍眼。终于,
她看完了最后一页。没有质疑,没有争辩,甚至没有多余的表情。她放下协议,
抬眼看向矮几的另一端。那里,早已准备好一支昂贵的钢笔。她伸手拿过笔,拔开笔帽。
动作有些迟缓,带着一种沉重的凝滞感。笔尖悬在乙方签名处的空白上,停顿了片刻。然后,
她俯下身,开始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白凤”。字迹是清秀的,工整的,
带着一种学生气的认真,与这满室奢华和他掷出的冰冷协议,格格不入。写完,
她轻轻放下笔,将协议推回到他面前。“王先生,”她开口,声音很轻,
带着一点点不易察觉的沙哑,像羽毛扫过心尖,却搔不起半点涟漪,“我签好了。”她甚至,
没有抬头看他一眼。王风拿起协议,扫过那个娟秀的签名,确认无误。心底某个角落,
似乎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地,是计划得售的落实,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轻松,
反而是一种更空茫的倦意。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很好。这间主卧归你,
我住隔壁。没有必要,不必打扰。”说完,他不再停留,拿着那份象征着界限与分离的协议,
转身,毫不留恋地离开了这个被强行布置成“新房”的房间。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
隔绝了两个世界。听到关门声,白凤一直挺得笔直的脊背,瞬间松懈下来,微微佝偻。
她维持着坐在床沿的姿势,很久,没有动。房间里那过分明亮的灯光,照得她眼睛发涩。
她缓缓抬起手,指尖无意识地抚过身上光滑冰凉的旗袍面料,然后,
轻轻握住了胸前悬挂着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小小的、样式古旧的银质戒指,
用一根细细的红绳穿着,贴肉藏在衣服底下,带着她微薄的体温。没有人看见,就像,
没有人记得。那个很多年前,蝉鸣聒噪的夏日午后,有个浑身脏兮兮的小男孩,
把一颗快要化掉的草莓味水果糖,蛮横地塞进一个穿着洗得发白旧裙子的小女孩手里,
凶巴巴地说:“喂,这个给你!不许哭鼻子了!等……等我长大了,肯定回来娶你!
听见没有!”小女孩捏着那颗黏糊糊的糖,愣愣地看着男孩被人拉着越走越远,阳光刺眼,
他的背影模糊在蒸腾的热浪里。那颗糖的甜味,仿佛还在舌尖残留。
可那个说长大要娶她的男孩,刚刚,用一份协议,彻底划清了他们之间的界限。他忘了。
忘得一干二净。白凤松开握着戒指的手,慢慢站起身,走到窗边,掀开厚重窗帘的一角。
窗外,是都市璀璨而冰冷的灯火,浩瀚如星海,却没有一盏,是为她而亮。
她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那个穿着大红嫁衣,却满面苍白的影子,极轻极轻地,
几乎翕动着唇瓣,无声地说了一句“王风,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一滴温热的液体,
毫无预兆地从眼角滑落,迅速没入旗袍立领繁复的盘扣之中,
洇开一小团深色的、不为人知的湿痕。王风搬去了主卧隔壁的客房。王府的下人们都是人精,
见状便知这场联姻的内里乾坤,对这位新晋的少奶奶,表面恭敬,背后却不乏审视与议论。
毕竟,一个来自“那种地方”的女子,如何能配得上他们天之骄子般的少爷?
白凤对此心知肚明,却并不在意。她依旧安安静静,
像一株不需要太多阳光雨露也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她没有试图去打扰王风,
只是默默地适应着王府的生活。她会仔细记下王风的口味偏好,在他难得回家吃晚饭时,
让厨房准备几道他多动了一筷子的菜;她会在他书房的窗帘换成更遮光的材质,
因为偶然听助理提过一句他最近睡眠不佳。变化发生在一个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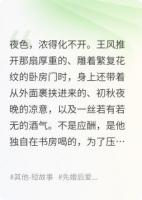 已完结
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