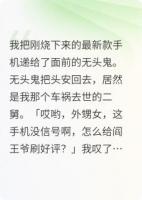3
段思源虽然有些富家公子的做派,但只要摸透了他的脾气,也不算难相处。
那就是必须要绝对地服从,他很讨厌任何人反驳他或者违逆他的意思。
在这一点上我做得非常好,甚至在知道他浅眠后,半夜里在二楼走动时都不会穿鞋。
我一直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处境,也知道自己有随时被送回福利院的可能,所以我必须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比起不苟言笑的老段总,段思源显然更合适一些。少年人嘛,嘴上再坏,心肠总是软的。
只要我足够听话,足够可怜,应该就不会被讨厌。
但段思源是一个不能用正常思维去考量的人。
他在偶然一次半夜撞到我又光着脚下楼去偷吃剩下的水果时,气呼呼地把我拉回了他房间。
“周一诺你搞什么?你总是做出这一副委曲求全可怜兮兮的样子给谁看啊?”
然后又自问自答:“哦,只能是给我看了,老段才懒得管这些。”
骤然被识破,我心口突突地跳,想要辩解两句又不敢开口。于是垂着头,做好了承接怒火的准备。
“说吧,你到底想得到什么?”
“……我只是不想再被抛弃……”
在短暂地看过某些全新世界、拥有过某些人和东西以后,我再也不想回到从前的一无所有。
段思源愣了愣:“谁他妈说要抛弃你了,我家养不起你吗?”
“那你能答应我吗?”
我问完就后悔了,甚至很多年后我也没想明白当时的自己哪来的勇气,那样任性而造次。
或许是惶恐之下的孤注一掷,又或者仅仅是因为拧着眉冲我嚷嚷的段思源,其实更亲切。
又想起去年圣诞节,叛逆小伙段思源偷偷跟哥们跑去喝酒,半夜才醉醺醺地回来,怕被老段抓住,竟然从后院翻墙。
要不是我提前关了红外线警报器,还一直守在院子里等着,他肯定要摔个狗吃屎。
段思源靠在我身上,灼热的气息喷了我一脸,等到将人放在床上时,我累出了一身的汗。
我久久凝视着那张脸,最后还是没忍住摸了一把,像是长久以来仰望的神明终于被凡人染指般生起隐秘快感。
如同此刻一样,让我控制不住生出些不合时宜的冲动。
段思源没有立刻回答,似乎确实在认真思考,许久才道:“我答应你了。”
寥寥几字,说得随意又平淡,我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不曾有过半分迟疑。
可惜,他最终却食言了。
用一张银行卡和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赶了我离开,甚至都没多看我一眼。
我带走了那张卡,是我和他之间的联系,却在哪怕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有花过那卡里的一分钱。
回到福利院办完了各种手续,我改名换姓,去了北方的一座三线城市读民办专科。
重新开始的生活对我来说,很苦又不算苦。只是累,暗无天日的疲惫。
我半工半读,再苦再脏的活都干过,最多的时候同时打四份工,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
时常会在洗盘子时打瞌睡,还在发传单时晕倒过,被好心的路人送到医院,却因为舍不得医药费而偷偷溜走。
坐在马路边上,喝五毛钱一支的葡萄糖,只要三支就可以支撑着继续工作。
大三时经朋友介绍,开始做一些平面模特的兼职,多了一些轻松的收入,状况好了很多。
那时我才恍然察觉自己就这么熬过来了,长成了一个世俗定义上的美女,还有了几个追求者。
其中一个还是富二代,我最不喜欢,因为总是让我想起段思源。
在又一次被我拒绝之后,那人恼羞成怒竟然动了手。拉扯间,我摔倒在地,右脸被地上的碎酒瓶划了一道大口子。
对方父母提出私了,说愿意对我进行赔偿,并且承担所有治疗及整容的费用。
我答应了。
比起让对方受到法律制裁,拿到一笔钱离开这里,对于我来说更为合适。
最重要的是我愿意整容。
七年间我深埋心底的思念被怨怼和不甘逐渐侵蚀,变成了扭曲的牢笼将我困于其中。
所以我想摒弃一切过去,用一张完全陌生的脸和全新的身份,再去见一见段思源。
哪怕只是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已完结
已完结